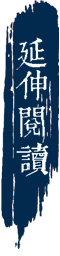所謂「集體非理性」,指的是一個群體在一定刺激因素的作用下,共同陷入一種偏離常態的情緒化心理狀態。正如勒龐在《烏合之眾》所描繪的,這種群體容易衝動、易變和急躁,易受暗示和輕信,情緒誇張且單純,偏執、專橫和保守,雖經常放縱自己低劣的本能,但卻不時表現出極高的道德。這種描述本來是用在大眾身上的,但當前的美國精英層幾乎完整地表現出了這些心理特徵。
作為現代理性「囚籠」的看守者和運作者的美國精英陷入這種集體非理性,是一種歷史的諷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這種理性「囚籠」的現實基礎是不可靠的,且其建構原則之間存在嚴重的衝突。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平等關係的理想性」要依靠「不平等關係的穩定性」來生存、或者說理想層面的理性要依靠現實層面的理性來生存。一旦這種「穩定性」出現動搖,這種「理想性」也就隨之衰減。二者是聯動的,現實理性的喪失導致理想理性的喪失,結果自然就是某種非理性局面,也就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美國精英的現實理性表現在2個方面:一是對國內大眾的穩定控制;二是對世界各國的穩定控制。然而,經過上一輪全球化,這兩種控制都出現了動搖。
首先動搖的是國內控制。從宏觀經濟指標上說,美國是這一輪全球化受益最大的發達國家,主要歸功於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和高端的科技創新體系。然而,這兩個體系賺取的財富高度集中化,而且吸納不了多少就業人口。所以美國出現了不是一般的貧富分化問題,而是財富寡頭化問題。「占領華爾街運動」喊出的「1%對99%」很好地概括了這種寡頭化趨勢。這意味著大量人口「階層下移」,中產階級「低層化」,資產階級「平民化」。尤其是像川普這種傳統的資本家在新的經濟遊戲中漸漸邊緣化,感到這個世界似乎已不在自己的手中,過去那種高高在上、悠然自得的控制感似乎沒有了,從而產生嚴重的焦慮感。他越吹噓自己很有錢,越是反映出內心的不自信。川普這種傳統商業精英的焦慮感是有代表性的,代表了精英群體中的一大塊。他們與低層化的中產階級在焦慮感上產生了共鳴,內心中都認為是這場新經濟遊戲的受害者。過去相互鬥爭的理性聯盟變成了共同發泄的非理性聯盟。歷史有一種殘酷的幽默。共同發泄的非理性就像一種傳染性很強的病毒,很快從經濟領域傳染到政治領域。政治領域的分權機制沒有對這種傳染起到抑制的作用,進入這個領域的精英很容易感染上這個病毒,而且要不停宣示自己感染才能在群體中生存下去。經濟對政治的作用在某種時候是通過這種心理機制實現的:經濟上失去的要從政治上找回來。這種「找」的過程更多地表現為偏離過去常規的非理性過程。那些本來「理性」的體制派似乎也被非理性的反體制派「喚醒」了,感受到理性控制的危機,並以不同方式加入了情緒化的喧囂之中。
接著動搖的是國際控制。二戰後,美國崛起為超級霸權;冷戰後,更是獨霸天下。基於現實強權的理性硬控制與基於自由平等的理性軟控制在國際領域更清晰地捆綁在一起。由於這種捆綁,人們常說的「雙重標準」也幾乎是自然而然的了。但其運作方式是動態變化的,當美國精英(主要是政治精英)對理性硬控制比較自信時,對理性軟控制的運用就比較正常,反之,就比較偏執。這一輪全球化產生了一個受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那就是中國。在計畫經濟年代,中國就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在全球性產業大轉移的過程中,中國抓住了機會,實現了工業體系的升級換代,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這種經濟轉型對於國家整體實力的提升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導致了以實力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儘管美國仍然是頭號強國,但美國精英對於越來越難以控制世界感到焦慮,這與川普之類的傳統資本家因失去國內控制而產生的焦慮是類似的。本來前者沒有後者嚴重,但美國精英為了擺脫國內控制危機的焦慮而將中國變成了共同發泄的對象。他們朝這個對象發泄得越多,後者在其心理中就越顯得像一個難以控制的敵人,於是又帶來了更多的發泄。這種發泄不僅僅表現為情緒化的語言,而且表現為非理性的行動。其突出的表現就是貌似受害者的強者去報複貌似受益者的弱者,而且不惜打破自己建立起來的、符合自身長遠利益的、也被弱者接受的理性規則。「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損人不利己遊戲在當前的美國精英層中頻繁上演。
美國一些自負和魯莽的所謂「鷹派精英」,無疑是非理性病毒的超級傳播者。起初,他們所傳播的主要是政治非理性,其背後還是保留了一點經濟理性。譬如說大規模減稅、迴避國際支出的責任等,不管政治後果如果,但對美國經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這也就是為什麼政治學者比經濟學者對此屆美國政府表現出更多反感的原因。
然而,新冠疫情加劇了美國精英的集體非理性,讓非理性病毒又從政治領域傳染到經濟和社會領域。疫情中美國民眾所展示的匪夷所思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傳染自美國精英的。精英和民眾的非理性行為最終損害了美國經濟和社會。今天的美國有點類似中國過去的王朝,精英們習慣了天下中心的感覺,一旦發現天下大變的時候,不是想著如何適應變化了的形勢,而是以不合常理的方式自我確認中心位置沒有動搖。於是,他們拋開軟控制,赤裸裸地展示硬控制的強權邏輯。然而,現實中的這種強權是有限度的,美國的諸類精英頻頻越過強權限度,一方面試圖獲得「小雞博弈」(參見儲建國〈面對戰略訛詐要有底線反擊的勇氣〉)的冒險收益,另一方面則讓世界面臨非理性失序的危險,最終危害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長遠利益。
面對美國精英的集體非理性,中國該如何應對呢?
首先感到吃力的是中國外交系統,你想講道理,別人不跟你講,你跟著罵戰,別人更加來勁,他們擔心的倒是耍潑沒人理。這個時候,中國外交系統和相關部門倒是可以冷靜下來,靜觀美國精英的耍潑。無論他們如何罵中國、整中國,我們只做出簡單明瞭的回應就行了,不要跟著他們的節奏浪費資源和精力。
譬如說,美國有那麼多的人想起訴中國,發起向中國索賠的訴訟活動,中國駁斥一下就可以了,千萬不能參與他們的司法過程。一個主權國家依據國內法在自己的司法體系中審判另一主權國家政府,除非經過後者同意或者把後者當作戰爭失敗國,否則都是對國際關係基本原則的侵犯。中國應訴就是默認這種侵犯,不僅是對中國國家主權的不負責任,也是對國際秩序的不負責任。那些主張中國應訴的人主要是法律領域的專家和律師,他們講的似乎有道理,但這種道理建立在對美國強權邏輯的無反思的默認基礎上。像沙特這樣的小國懾於美國的強權,不敢抗爭。中國則要負起這個責任,中國不做美國的敵人,但可以做美國不公正行為的校正者。美國說中國是修正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這個詞也沒有錯,只是中國是將國際秩序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修正。中國可以就主權豁免問題同美國進行磋商,但決不可接受美國單方面否定中國主權及相關權益的行為。
既使這種校正者,中國也需要有策略地去做。川普宣稱「有原則的現實主義」,這個詞用在中國身上倒是合適的,用於當前的美國不合適。當前的美國精英奉行的是「非理性的現實主義」。中國講原則,但也要根據現實的力量和條件去做事。對於美國精英的諸多非理性行為,中國沒有精力和能力去校正,只能冷靜觀察,但對於嚴重侵害中國核心利益,破壞國際關係基本原則的行為,中國則一定要守住底線,堅決鬥爭。
對於一些美國人起訴中國的司法過程,中國可以保持不理睬、不參與的態度,但是對於美國國會試圖通過取消中國主權豁免地位的立法活動,中國需要堅決鬥爭,全力反擊。因為這種法案的性質類似《臺北法案》,是對中國主權和國際秩序的嚴重侵害,且具有長期效果,這種效果不是一、兩個官司可以比擬的。《臺北法案》在討論、審議時,中國外交系統有鬥爭不力的地方,當前武統情勢升高與前期鬥爭不力有一定的關聯。沒有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持續有力的外交鬥爭,陷入集體非理性的美國政客就不太可能意識到其行為的危險性,就容易跨出越過底線的一步。當中國真正做好武統臺灣的各項准備,隨時可做出武統決定時,美國有關政客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謂美國「五.二〇聲明」才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承諾保持與臺灣的非官方關係。
總結《臺北法案》出台的教訓,中國外交系統一定要對類似的立法動議密切關注、深入研究,以便做出及時有力的反應。1如果仍然犯類似過去的錯誤,讓取消中國主權豁免的動議過關,那麼中美關係就會真的破壞到難以修複的地步。
所以,面對集體非理性的美國精英,中國有關方面在冷靜觀察的同時,一定要守住底線。守住了底線,就可以防止美國精英的集體非理性對中國核心利益帶來難以挽回的傷害,並在此基礎上,可以尋找中美之間、中西文明之間新的共處方式。不同文明之間有諸多共通之處、有諸多互補之處,中國悠久的歷史就是不同文明要素相互融合的歷史。中國越是學習西方,就越能夠準確發現自己文明的優缺點,越能夠取長補短,越能夠創造出新的文明要素。相反,美國精英在非理性的言行不斷自我否定,不斷丟棄西方文明中的優良因素,使自己的國家朝著劣質化的方向發展。
就這次疫情防控來說,中國的相對成功之處一方面在於更好地發揮了學自西方的科學精神,遵循了疫情防控的規律,另一方面更好地將科學方法與自身的制度特點結合起來,沒有像美國那樣出現科學與政治的嚴重衝突。這就是中國在學習外來文明的過程中,將內外優勢結合起來的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儘管也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這些不足是可以在未來的日子裡不斷加以改進的。而在很多美國人那裡,一旦中國被視為某種壞的國家,那麼這裡所發生的一切似乎都是壞的,本來比較成功的一件事被當作失敗的典型到處宣揚。這樣偏執的結果在傷害中國的同時,也給美國帶來巨大損失。如果美國認真對待中國抗疫經驗,結合自身特點,學習其中可以學習的東西,那麼美國就決不會付出那麼大的生命和經濟的代價。然而,集體非理性讓當前的美國沒有可能做到這一點,這是巨大的悲劇,但眾多的美國人還認識不到這一點。劣質化的美國精英對此要承擔歷史的責任。
當然,我們不能把在特殊時期的情緒和表現加以固化,視為某種長期性的因素,美國自我校正的能力還是比較強的。這個國家不憚揭別人的短,也不憚揭自己的短。某些短處被揭得多了,也常常會得以改進。當前美國精英的這種集體非理性肯定不是正常的狀態,他們終究是要走出來的。當他們恢複正常之後,美國又是怎麼樣的美國,中國人也許會感興趣,但中國人更關心的是,受這種集體非理性傷害的中國又會是什麼樣的中國。我們守住底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致命的傷害,我們冷靜觀察的目的就是要分清短期和長期的因素,認真思考未來長期的中美關係該如何去處理,如何更好地對西方文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努力創造出一種更可持續的新文明。
中國人有這種偉大的抱負和實現這種抱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