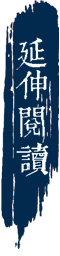(肆)「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貨力為己」,
而「治著太平」、「天下為公」之嚮往無已,
卻在潛滋默長否定之否定
為本文所提出之研討主題,若中國社會根柢之天下體制、天下哲學,如只限定於這樣的一段歷史時期──從中國有史之初的夏代起,到先秦之春秋戰國時代止,則本文的研討到了上一章節的結束,當可說已告完成。
然而不然,本文之作,當非一弔古的詩篇,視彼為往聖前哲所奠立之天下體制及其哲學,到了秦漢時代已告死亡,我們在今天偶發懷古的幽情,用以憑弔陳迹者。相反地,乃是有見於日告顯著的歷史徵象,中國社會之於近世和當代,似在其試錯而進之中,一「反」秦漢以來的社會形態及其內涵之為中國古代社會之「反」,而要另為開出一個高層次之「正」者的新局來。合古今及未來而統觀之,中國之歷史全局似要完成其由「正」而「反」,再由「反」而「合」之辯證發展。以上數章節的探討,在側重於先識其「正」。因為識其「正」,才能識得秦漢以來的社會為中國古代社會之「反」,亦才能正確地辨知並進而主導,今日和明日的中國社會之究應或究宜何去何往。
事實上,要否定中國之中古社會和下古社會的思想種籽,亦即要反秦漢以來,甚至夏商以來,中國之社會體制及其意識形態的思想種籽,堪稱之為中國社會哲學的「反」之「反」者,是早已潛播並默長於秦漢以來的社會制度及其識形態的母體之內。顯而易辨的矛盾,則為:「天下為家,貨力為己」之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於夏商以來的中國社會,尤其是於秦漢以來的中國社會,固居於統治的地位,然而,生活於此類社會機體之內的仁人志士,卻並不視其為事理之當然應然,相反地,他們不只是斥其為「今大道既隱」之反常,且時時眷懷「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治著太平」的盛世,而興發強烈的願望,希其能夠重視於他們所處的各當代。
是二者殊途而同歸,歸向於中國社會之「反」之「反」,其將終要為今後的中國社會開拓出一個高層次之「正」來。
一、
於「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為義,及「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貨力為己」之為義,各予以簡明而賅要的陳述,且並把它們放在一起,作出鮮明的對比,當為《禮記・禮運篇》(此文之撰著,約在秦漢之際,或西漢初年,出於孔子弟子言偃學派之後學)首段的傑作。其說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1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2,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己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3,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4,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5。故謀用是作6,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7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8,著有過,刑9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10。是謂小康。
上所引文,雖不過三四百字,然於其具體、明確而且極其生動的對比之中,此類之兩個歷史時代,兩種社會制度及其精神意識之不同或迥異者,不只是明白如畫,可使讀者感到深刻的印記,更重要的〔是〕,前者之優於後者,異常突出,而尤具說服和號召的力量。
此所以兩千餘年來,身受後一制度之害的人們,以及各時代有正義感責任感的仁人志士們,每讀此文,不僅是會為之廢書而嘆,嘆今日之「大道既隱」,且不乏投筆而起之人,要旋乾轉坤,推此後者之速去,讓彼「暫隱的大道」得能再度地重現,運行於當代和後世。
大道之曾運行於上古,若似一個千真萬確的史實,自在大大地增強著秦漢以後各時代反叛者的信心,且在增益著他們之經濟的、政治的、甚至道德的自覺。
待到後漢,何休的「三世說」,若「據亂」、「昇平」與「太平」云云「三世說」11的出現,不只是加速了此類已轉入於地下活動之天下哲學的潛流之流行,且使此類的潛流像浪潮一般地此伏彼起,先向「著治太平」這一面衝擊,以爭取大眾生活之豐裕均平。
這是一種甚為特殊亦極其錯綜複雜的歷史態勢和力量,曾經支配中國歷史波動者近兩千年。欲知其故,或尚須先作一番掘發、辨析和綜合的工作。我們且來研討一下何休的三世說。何休的三世說,是承繼春秋公羊家的傳統,視春秋時代之於孔子為「所傳聞」、「所聞」、「所見」的三世說而來,而並予以更進一步的推演。其說云:
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故內其國,而外諸夏。……
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
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
何休的三世說,見於他所著之《春秋公羊解詁》魯隱公元年傳注。單依何氏的本文以看他的三世說,很易了然,為其所劃分之「據亂」、「升平」和「太平」云云之三世,均屬側重於夷狄與諸夏之間民族關係或退或進者以為說,這當是屬於中國天下傳統的正脈;然而卻似無關於人民大眾社會生活之豐裕或貧乏,均平或不均平。
既是如此,則何休之「太平世」,竟何以會對東漢以來,歷代爭取社會均平之太平運動,發生若彼巨大的影響,似屬不可解之謎。
於此困惑,若欲達致正確的了悟,在我們或須要跳出於何氏的一家之言之外,就其邇近和更遠的背景作進一步的探求。事之趨於錯綜複雜者,或係由於何休之巧於改造《太平清領書》12之太平說,用「著治太平」的「太平」以名其三世之最上世,並以「見治升平」的「升平」,以名其次於上世的中世;於無言之中,他的三世之上世和中世,已同《禮運》所稱之二世,若「大同」與「小康」者,發生了息息相關的關聯。唯其如此,由於「著治太平」的附益,更增加了人們對於「大同」之世的嚮往。倒轉過來,此「著治太平」之「太平」,與之相應地,也被浸入了「貨力不為己」,人人均應獲得豐裕均平之養的思想成分。
但此類溝通二者的橋樑,卻非何休隻手所搭成,應注意的前於何休和于吉的典籍(編按:即,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于吉的《太平清領書》)已有盛言「太平」之義者,且其為義多與人民大眾社會生活之應該豐裕均平者相關聯。例如於《白虎通義》,為符瑞、禮樂、封禪、巡狩等篇所分別傳述的太平義13,不下十數則,類而分之,可得三類:第一類為不分夷夏、「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的太平;第二類為人民大眾社會生活之均獲豐裕均平之太平;第三類為不分夷夏、「天下遠近小大若一」,而人民大眾的社會生活又均能獲得豐裕均平的太平。14在這裡,我們或須對於東漢初葉所舉行之學術集議,若白虎觀集議15者,表示謝意。這次集議的主旨,在考定五經的同異,故曾廣事搜求且兼容並包散逸民間之古說和新義。而其結果,原同秦漢社會及其意識形態不相協調的太平諸義,也被發掘著錄,流傳下來,且復居於同經典的地位。
若上溯之,並可知悉,為《白虎通義》所傳之二三兩類的太平義,當亦非漢人之所臆造,實上承西周經典所已隱約道出的太平義而來者。若《詩經.小雅》之〈魚麗〉,《大雅》之〈鳧鷖〉,即其根源。於〈魚麗〉,詩序云:「〈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毛傳》則云: 「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於〈鳧鷖〉,詩序和《毛傳》有著同上相類的序解。詩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毛傳》並云:「太平,則萬物眾多。」應注意的是,此二詩之異曲同工。前者假魚類之眾多以喻萬物的豐盛,再借萬物之豐盛以喻天下之已告太平。後者則假鳥類之眾多以喻萬物的豐盛,再借萬物之豐盛以喻天下之已告太平。待至此類的觀念由魚鳥而及於穀物,太平云云之意義和名稱已於焉成立,如像《漢書.食貨志》所傳之古說:
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16
如上所述之表意方法和過程,固甚樸拙,然而,其為「天下太平」概念之所由出,卻極其真實而具體。從這裡,我們不只是由以理解,概念意識之為物,其產生殊不易易17,不可能憑空出現;更重要地,且並可進而知悉,即於西周時代,「天下為均」、「天下為平」即是「天下之政」之「政在生成、化成」者,實並蘊「政在養民」之義,而此「政在養民」之「養」,應是豐裕均平,而且以天下為其範圍者。
也唯其如此,為何休所提出的「太平世」,其內涵雖只限於太平三義之第一義,亦即《白虎通義》所傳太平三類之第一類,然而,名見義備,有關「太平」云云之諸義,即齊頭並現,「社會豐裕和均平」的太平義,似尤為突出。何休的「太平世」之提出,抬高了于吉《太平經》的地位,大大地加速了人們對於「社會之應豐裕和均平」的嚮往和爭取。幾經蘊釀,到了東漢的末世,「太平」云云之側重於社會制度大眾生活之理應豐裕均平之義者,不翼而飛。其於社會大眾在生活方面未能得其豐裕均平之人,直不啻一響亮的號角,在呼喚他們,起而造反,以爭取社會生活之豐裕均平,且並可親身經歷一個太平盛世的到來。
達致上述的認識,或始可正確理解:從東漢末世、三國初期出現之太平道式的太平運動開其始,通過唐代的王仙芝,宋代的王小波、李順、莊綽、徐夢華等人之太平民變,到洪秀全之試建太平天國,其主題之所指,何以均屬於社會之應豐裕均平之義的太平嚮往和爭取。
到了當代,中共之領袖人物,若毛澤東氏者,以鄉村中的農民代替都市中的工人,從事於其所稱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而在我們來看,這與其說是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倒不如說它是中國的太平主義、太平運動的現代化。1949年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似可視其為中國式的太平運動之已達致其有史以來的最高潮。
此類高潮之達致,當已使秦漢以來、或夏商以來,中國社會之為古代社會之「反」者的某一面,亦即「今大道既隱,……貨力為己」者這一面,發生相「反」的變化,並已顯而且著地呈現出一種堪稱為「反」之「反」者的新局面。
二、
秦漢以來,尤其是西漢以後,作為中國社會哲學,亦政治哲學的地下伏流之一,若太平主義、太平運動者,其內涵並不只限於人民大眾社會生活之豐裕均平的一面,且並指向於民族與民族間之「天下遠近小大若一」。這是本文前曾鄭重論及者。於這方面來看當代中國之革命成就,自仍有其可批評應批評的地方。例如豐裕均平之為太平主義的一面,中國古人所側重於豐裕者多,而今人則視均平為重;推至其極,竟向均平觀念之極端處倒,構成一種均平壓倒豐裕的態勢,似已不無出現了「均貧」「均苦」之失。而於種族間之「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則今日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地位和生活之有顯著的改善,當其應予稱頌的業績;然於外蒙問題、西蔵問題,尚未能夠作出高境界的處理,以消除外國的干預。在今日的東亞,即來奢談大於中國之「遠近小大若一」的太平,固不無言之過早。但若識及天下思路和天下格局之為物,或並為今日世界、今日東亞之所需,似亦應於高瞻遠矚、智及未來的仁智之中,修正自己,以適眾適,為一個更廣大地區之「遠近小大若一」的太平境界之可能出現而構思。
公平論斷,亦自不應求全於一人,責備於一黨。若從秦─清之間的歷史來看今日的中國,當不容不承認,其在社會的太平主義的實踐方面所已達致的成就,是相當輝煌的。
但當我們的探討來到了這裡,卻尤應進而知悉的:太平主義及其運動之出現於兩漢,及其以後,固然是來自民間,為一種大眾性的社會思想。然而,至堪注意地,於某種的限度之內,社會大眾之均能獲得豐裕和均平,不只是於王朝的統治者無害,且甚有利於他們的統治。以此之故,純經濟性的太平主義,不獨是不為王朝所排拒,更微妙地,與「五穀豐登」相聯的「天下太平」,並為歷代王朝之共同願望、官方哲學。從秦漢到明清,出現於中國歷史上的王朝眾矣,然而幾可說,沒有一個王朝不在希望著,人民大眾,亦即所謂黎民百姓者,能夠家給人足,共享太平者。不只是希望而已,且有不少開國開代的英主們,在這方面從事於實踐的努力,以求致之。
此類的史實,當復更深刻地向吾人透示歷史的秘密:兩漢以下,出現於歷史的太平主義、太平運動,有其主要的民間的一面,也有其官方的一面;然即係來自於民間,太平運動所要反對、所要改變的主題,似只在「今大道既隱,貨力為己」的這方面。因而,此類的太平運動並不必然地蘊涵另一類的基念,要推翻「今天下為家」之世襲王朝制。太平天國是一個顯例。然亦唯其如此,秦漢以後,中國天下哲學之轉入於地下活動者,還在平行著另一系列的潛流。那就是: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然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天下為公」卻反為大家之所嚮往無已。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云云之為說,當非出於〈禮運篇〉作者之個人的幻想,乃屬實有其所指者。其所指,就是中國古人之共同相信,並共同仰慕的唐虞盛世和堯舜之治。而所謂唐虞之世與堯舜之治,亦非是無根據之譚,依吾人之所理解,當正是中國氏族社會時代的氏族民主制。這是我們應該特加注意的史觀,中國古人在這條路線上看古史,不只是出現為《孟子・萬章篇》所傳之批史: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
及為《韓氏易傳》所傳之判史:
五帝官(公)天下;三王(夏、商、周)家天下。18
更明確而具體地,於我們前所徵引之〈禮運篇〉,一向被人們所推崇的聖王,若禹、湯、文、武之治與世,亦只能許之以其為「今大道既隱」之後的「小康」之治與世。他們之為人也,也不過是「三代之英」而已矣。
禹、湯、文、武之被貶抑,不是他們沒有大的貢獻,卻只為一個「家」字,亦即是一個「私」字之所累,改變了前此的「天下為公」者,而成為「天下為家」了之故。
「天下為公」代表著「大道之行也」,而「天下為家」就是反映著「今大道既隱」。兩相對待,兩相比照,當已給「天下為家」之繼續存在以嚴重的打擊。這類的打擊,是政治的打擊,道義的打擊,亦一邏輯性的否定,使其日益處於不利的地位。秦漢以來,中國古人在這方面從事於理論性的闡發者,不乏其人,於〈禮運篇〉的作者19以下,若阮籍、鮑敬言、黃宗羲、唐甄等人,即其上選。
到了吾人的前一代,從理論之試為提出,而並予以現代化,到躬行實踐地試之以革命,以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能再現於中國,且並曾獲得最初步的成就者,孫中山先生堪稱為一位最突出的大人物。
但是,孫中山先生之去也,已屆滿半個多世紀,而「天下為公」之來也,不只是遲遲其行,且不無可能要誤於有理論的倒退。
我們自應知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再度地回返於中國大地,不只是意味著,要完成反秦漢以來中國社會之為古代社會的「反」之「反」,且並要完成反夏、商、周以來中國社會之為上古社會的「反」之「反」。當無怪其積重難返。
然而,我們亦應知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再度回返於中國,乃是中國社會由「正」而「反」,再由「反」而「合」之正常發展之邏輯的必然。因而,其將終於再來,亦是一個邏輯的必然。
如何突破並解放當代中國或舊或新之意識藩籬、思想局限,以大以闊男女老少的心智,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能再還於中國,亦即是為一種符合於中國歷史要求的民主制度之能運行於今後的中國,舖好道路,當屬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或下一代的中國人,應負的大責,不容旁貸。然而,我們亦應知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再度回返於中國,乃是中國社會由「正」而「反」,再由「反」而「合」之正常發展之邏輯的必然。因而,其將終於再來,亦是一個邏輯的必然。
如何突破並解放當代中國或舊或新之意識藩籬、思想局限,以大以闊男女老少的心智,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能再還於中國,亦即是為一種符合於中國歷史要求的民主制度之能運行於今後的中國,舖好道路,當屬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或下一代的中國人,應負的大責,不容旁貸。(全文完)